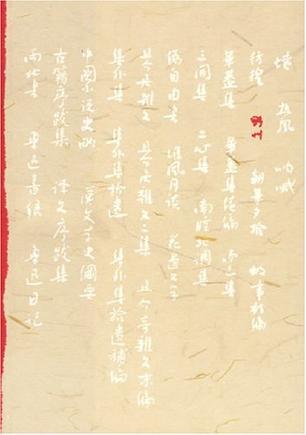-
遗憾的是,中国的“性学”使用者与传播者,支持者与反对者,却基本不了解,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,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,在一些性/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。在这种混淆之下,一些人,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,不管理念如何,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(实为错爱);另一些人,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,不同的是,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,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天元对立式理解(最初是用“性权”对立于女权,后把性权改为“性学”)。情感迥异,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: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“一刀切”。
-
遗憾的是,中国的“性学”使用者与传播者,支持者与反对者,却基本不了解,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,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,在一些性/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。在这种混淆之下,一些人,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,不管理念如何,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(实为错爱);另一些人,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,不同的是,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,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天元对立式理解(最初是用“性权”对立于女权,后把性权改为“性学”)。情感迥异,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: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“一刀切”。
-
遗憾的是,中国的“性学”使用者与传播者,支持者与反对者,却基本不了解,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,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,在一些性/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。在这种混淆之下,一些人,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,不管理念如何,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(实为错爱);另一些人,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,不同的是,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,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天元对立式理解(最初是用“性权”对立于女权,后把性权改为“性学”)。情感迥异,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: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“一刀切”。
-
遗憾的是,中国的“性学”使用者与传播者,支持者与反对者,却基本不了解,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,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,在一些性/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。在这种混淆之下,一些人,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,不管理念如何,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(实为错爱);另一些人,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,不同的是,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,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天元对立式理解(最初是用“性权”对立于女权,后把性权改为“性学”)。情感迥异,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: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“一刀切”。
-
遗憾的是,中国的“性学”使用者与传播者,支持者与反对者,却基本不了解,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,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,在一些性/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。在这种混淆之下,一些人,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,不管理念如何,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(实为错爱);另一些人,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,不同的是,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,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天元对立式理解(最初是用“性权”对立于女权,后把性权改为“性学”)。情感迥异,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: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“一刀切”。